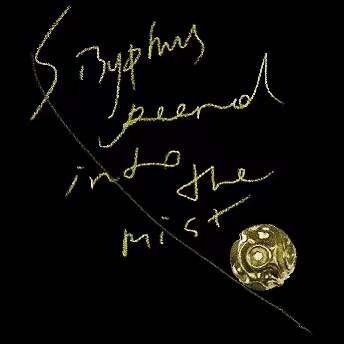时间来到2019年末,熬过漫长的找实习焦虑期,渴望逃离现状驱使着我直直地跨进了一面拥有一个大大的“画”字的墙,兴奋地叫了一辆货拉拉几乎把半个宿舍搬了过来。当时的我像一只逃亡的虫子,哪里可以安身我就往哪里钻,离开学校宿舍的身影十分得意,活像长了尾巴一样哗啦哗啦地摇。
拿到408的宿舍钥匙,爬上摇摇欲坠的床,铺开重重的冬被,我在想,我从一个宿舍逃了出来住进了另一个宿舍,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根本没什么改变?那么我都在开心些什么呢?展望的新生活真的如我想象的那样,顺利成为我踏上理想之桥的垫脚板吗?
我对和人搞好关系这件事一直很困惑,长大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有“关系好”和“关系不好”,“熟”和“不熟”这两对选项。复杂的多线选择题中,也有像我前室友那样熟但是互相厌弃的,我讨厌维持虚伪的和谐场面,这种关系就像我网购买到的低级日用品,一般只在它终于分崩离析的时候将其丢弃。
新室友们似乎还没下班,我打量着全身镜,镜子中整整齐齐地摆着室友的鞋,都很好看,甚至让我觉得它们摆在这片水泥地上不太合适。
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低着头,因为不想过多探视室友们的隐私只草草地看了一眼这间屋子。真好,有一面窗子,窗外是曲折的小路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又住了一间没有阳光的房子,至于朝北还是朝南,我不知道,因为我一向分不清东西南北,我的脑子里只装得下最近生活里需要用的知识。
/
《阿丹》
低着头,我看到了一双黄色的休闲鞋,眼睛还没来得及往上扫,我就知道这双鞋的主人可能是女同性恋,这样说可能对她有些冒犯,但我往上看到她的脸的时候,着实松了一口气。她端着一只锅跑进来,是的,一只锅,我刚想问这里有厨房吗,她立马和我搭话:“你是新室友吗,她们都还没回来,我带你看看厨房吧。”
我们交换了名字等信息。阿丹的皮肤很白很嫩,几乎看不出年龄,此刻,除了名字和出生地我对她一无所知,但我竟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丝丝我自己的影子,我说不出来缘由。
彼此出柜后,我和阿丹熟起来不过是两天的事,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被分在一个组里,所以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实习生干的大部分都是体力活,阿丹告诉我,以前这些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的,不会像现在这样还有人帮忙。她说话的语气中没有得意,也没有炫耀,但给我心里带来一些宽慰。我想,她这样瘦瘦小小的身体都蕴藏着如此坚韧的力量,我又有什么资格再去喊累呢。
阿丹是从设计岗辞职来的,因为喜欢胶片外加想摆脱工作压力,跑来这里开始了这段报酬并不高的实习生活,设计岗的工资应该不少吧,当时的我心想。
平日里的阿丹总是一头黑短发顺顺的,直到有一天,记得那是在年会前一天,公司的空气里已经弥漫着快要下班的喜悦和悠闲。她梳着油头登场了,我才知道她把她的发胶也借给了同期的一个男实习生,只不过阿丹会把头发梳得光光亮亮,齐齐整整的,而他因为不熟悉把头发喷得一绺一绺的,像七八十年代为了参加毕业舞会偷用老父亲发蜡的初中生。阿丹的油头,油得可爱,称得她的脸也变成了水光肌。
阿丹走的时候把她的锅过继给了我,后来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我用它煮了数不清的意面,丸子,有时望望她的床,好像那个会在晚上在床上点灯安静打坐,有时反应居然会比我还慢半拍的女孩从来没跨出这扇门,每当又遇到什么趣事,我会想知道,说给阿丹听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日子又会多添几分乐趣。
/
《yangyi》
按照认识顺序的话,yangyi应该算我最后一个认识的室友了。在见到她之前,我在408另两位成员那里听到她不在的理由是:她背着相机去爬山了。
第二天,我心想今天总能见到她真容了,往她的床瞄了一眼,她整个人平躺在厚被子里,我就这样盯着十秒,发现她一动也没动,最后开始怀疑这张床上到底有没有人在。
阿丹走后,我和yangyi就几乎天天被分到同一个组里,也就渐渐熟起来。
过了这么久,每当想起她,我的脑海里只能浮现出jerry鼠的模样,她的笑容很能感染人应该也得益于此吧,也因为这样给她添了几分机灵相。
Yangyi喜欢戴一顶皮制的贝雷帽,黑黑的亮亮的,疫情期间戴上口罩整张脸就不剩下什么可见内容了,她对此感到很轻松,把合照里的自己全都裁掉也是她会干的事。如果说阿丹的鞋子就可以让我判断出她的气质偏向,那yangyi的性别气质是真的很模糊,和她相处很容易就会忘记她的性别设定,她愿意扎马尾但只是那样做很省事,她喜欢穿格子衫但只是那样穿很舒服。
和yangyi分在一个组的日子很轻松,因为性子软,我已经不太敢在人前展露出我时不时的迟钝、甚至一些愚笨的表现,搬进408后让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假装强悍,不用担心被侵占任何东西,和yangyi之间有一种默契,就算互开玩笑也是恰到好处,既不辛辣也不无趣,消磨了一块又一块的枯燥的工时。
她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拉着箱子走出这座楼时,我心想,一定会在别处再次见到她,以创作者的身份。
/
《江江》
江江是我第二个见到的人,彼时的她披着一头艺术气息非常浓厚的长卷发,戴着一顶贝雷帽和一副圆圆的眼镜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和yangyi的帽子不同,她更喜欢戴麻布做的。而她不仅有这顶帽子,在她挂帽子和收藏衣服的地方总是能让我们见识到一些小的新奇玩意儿,就像霍格沃茨里的luna,让你不禁好奇你和她是来自同一个空间吗,她会魔法吗。而我回身瞅瞅自己的衣柜,只是胡乱地塞了些合乎季节的衣服,黑压压地成了一片让我每天都没有动力打开。她周身透露出对美的理解,审美的一些细微关照有时让人眼前一亮,有时又随意得恰到好处,让人不自觉地开始关注她的个人风格融进平日生活里的样子。
江江比我大几岁,后来知道这一点的我有些惊讶,因为我一向觉得她只是一个和我同岁但已经有自己的生活姿态的人。也因为她我才知道,原来人生不是用年龄来丈量的,进入社会也不一定会被完全改变,被所有企业文化唾弃的“学生味儿”是一片用来体察世界的滤镜,它可以被暂时摘下但任谁不忍心将它践踏,当我们踏入明媚的春光里,我们还是会蒙上它,给记忆染上一层葱绿色。
Yangyi走后的日子,我和江江总会寻着一起调休的机会溜出去闲游,在动物园里她会关注一只倚靠在圆筒上看起来身心俱疲的熊,在工业区里她会把一只野猫脖子上紧缚着的锁链解开,依仗着这一套看世界的眼光,和她一起走在休息日的路上总是开心无忧的,使人不由得贪婪起来,想要一直缩在这理想国中。
但仔细一想,说这是理想国,是因为我们忙碌后偷闲的闪光生活,虽然体力劳动居多,但我们凑在一起聊的是周末跑去哪里拍照,哪部电影好看,动森怎么玩,乐队的夏天又出了,后院又来了一只流浪猫,仿佛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是为了那两天的生活而存在的。
后来我偶然听说,曾经有一个实习生兴致勃勃地来到这栋小楼,第二天就连夜卷着行李一边哭着离开了。这让我想起从朋友那里听说去杭州蜂巢剧场实习的朋友,带着对戏剧的憧憬、热爱,对孟京辉的欣赏、崇拜而来,离去的时候胸中的理想图纸被现实撕得粉碎。
我能理解她们,并不觉得她们玻璃心,或是久居象牙塔后对理想世界固执地信任,我能理解她们,因为也有一个这样的小人住在我心里,只不过我发现我渐渐地,连理想破灭这出戏都没成本表演了。
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渴望通过创作来摸索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边界,寻找和世界相融的可能性。还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会把喜欢的东西定制成徽章挂在书包后方,虽然从未展露出来,但心里总以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是有趣的,别人都是无趣甚至平庸的,在一个小型的社会里一心想钻进更小的舒适圈。来到这儿我发现并不是这样,有理想的人并不少,有些人只是默默地在做一些微小又勇敢的事,她们的理想之灯也从未熄灭。
我们会再相见的。